老侯
錯誤的第一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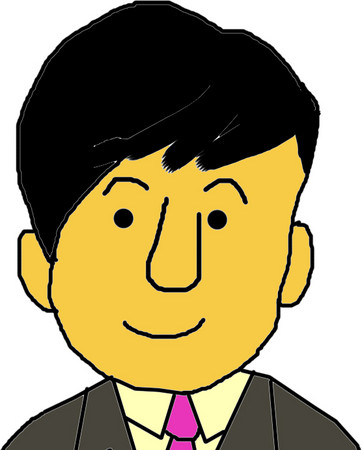 我在日本,向公司提出辭呈,算算有20多天的休假要消化,加上周六、日,足足一個月。
我在日本,向公司提出辭呈,算算有20多天的休假要消化,加上周六、日,足足一個月。
辭去工作,「有薪年假」還沒消化完,一般就把離職日定在年假消化完的那一天。這段從離開工作到正式離職的休假日子,日文稱「有給消化」。「有給」,就是「有薪假」。
我利用這段休假期間,在東京家中養了幾個禮拜的浩然正氣,心寬體胖,再回到久違的台北探望家人,又受人之託去了一趟上海,藉此領了一點酬勞,最後回到日本,繼續休假。
這趟上海兼差之旅,讓我犯了一個「致命的錯誤」。只因這一節,有分教:「小員工慚懼惴惴畏橫禍;大律師雄辯滔滔挽狂瀾」
我離職的公司有一條內規:「不許兼職」。「不許兼職」的理由很簡單,怕你洩漏公司機密、怕你有利益輸送、怕有競業之虞…總之,為了防患於未然,公司和每個員工都定了這個「不許兼職」的合約。
這「不許兼職」是個非常嚴厲的「天條」。有看倌說:「景氣不佳,公司分紅也少,我去便利商店兼個差貼補家用也不行嗎?」答案是不行。過去就有人曾經為此,被公司處分。
我雖然離開公司,電腦等用品也都還給公司了,但仍領公司的薪水在休假,「形式上」仍是這家公司的員工。我拿公司薪水的同時,又從別處拿了酬勞,我就是成了「兼職」的現行犯。
這事情,我一直等到25日領薪水,才突然想起。
我不知道這可能會多嚴重。兩邊都繳所得稅,遲早會被發現(事後證明是我多慮)。
一些可怕的場景出現在我腦海。我可能被公司一狀告進法院,要求我賠償損失、甚至罰款;我在日本留下訴訟紀錄,影響我此後的就職…等等。
我打了一個電話,給一個曾在某家公司人事部工作過的朋友,麻里小姐。
「你怎麼會做這種事?很沒常識,你知道嗎?」麻里毫不掩飾她的驚訝,在電話那端數落我:「我不知道要怎麼幫你!日本人絕不會做這種事的,我也從沒處理過這種事。」
短短幾句話,我被她說得抬不起頭。尤其涉及到「我們日本人」、「你們外國人」這類的話題,更是有理說不清。出門在外,無論如何就是沒辦法讓人以一個獨立個體看待,動輒就把個人問題上升成了「國際」問題。
「那麼,我主動承認自己兼職,承諾退還薪資,是否就能解決了?」我如洩了氣的皮球一般,無奈地提出我的「解決方案」。
「我不知道,這就要看你們公司的規定了。」麻里說著,口氣已類似「看好戲」了。
和麻里通完了電話,我人猶如虛脫般坐在椅子上。為了離職,我已經放棄唾手可得的年終獎金;要是連這一整個月的薪水都退還給公司,這個失血量大得驚人,幾乎要影響生計。
我硬著頭皮,打電話給我原先的老東家。
公司人事部的小姐,接起了我的電話。
「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元○○部の侯と申します(承蒙照拂,我姓侯,原先在貴公司○○部任職)。」
一般公司同事通電話,是「對內關係」,開頭是說「お疲れ様です(您辛苦了)」;一旦離了職,關係立刻「打回原形」,成了「對外關係」,招呼語也變成了「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(承蒙照拂)。」時時注意和對方的相對關係,是日語重要的組成規則。我們老外講日語,一半精神花在釐清彼此關係上。
「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(承蒙照拂)。」人事部接電話的小姐也行禮如儀。
「對不起,是這樣的…我才離職不久,目前還在有薪假期中,一時疏忽下,兼了一份差…。」
接電話的人事小姐一聽,慌了,似乎完全不知怎麼處理,電話那端傳來異樣的沉默。
半晌,人事小姐總算開口:「這…這我得問問看。您稍待一會兒,我們再回電話給您。」說完,隨即匆匆把電話掛了。
我無疑投下了一顆震憾彈。
不久,一位自稱山口的人事部小姐打了電話給我。我們做顧問的,一年到頭難得回公司,人事、總務、會計…這些部門有哪些人,我們經常搞不清楚。
「侯桑,您好。聽說您現在在兼職?」
「我…沒錯。但是,只賺點外快,沒繼續做了。」
「恩,這樣呀。您也清楚,我們公司是不能接受兼職的。我們研究了一下,今天25日,這個月薪水現在已經匯到您的戶頭了。目前最穩當的作法,就是您將這個月的薪資退還給我們,我們可以把您退職的日期提前到3月底,讓您的在職期間不會與您兼差的日子起衝突。不知道您的意思是…?」
山口條理分明地把他們的「提案」說給我聽,無非就是要我把幾十萬日幣統統吐出來。我腦子一片空白。我還在規劃下一份工作,在那之前,我不知道這沒收入的日子還要過多久。如今要我把錢吐出來,無異是要割掉我身上的一塊肉。
但我有別的選擇嗎?這麼大的公司,要告倒我,不就像是捏死一隻螞蟻一般的簡單?
我在電話裡回答:「好的,我…我會將錢還回公司。」
山口說:「好,有您的同意,我們事情就好進行下去。我們會寄『請款書』給您,您按照這『請款書』上的金額、銀行帳戶付款。我們收到款,就會把您的正式離職日改到3月底,幫您省去麻煩…。」
掛上了電話,我發呆了好一陣子。錢,看來是非還不可了。在收到「請款書」之前,這筆錢,我還有一段「鑑賞期」。房租靠它、水電瓦斯也靠它,現在卻看得到、用不得。
道道地地的「因小失大」。本該是輕輕鬆鬆過著有薪假的日子,卻因為我惹來的禍端,變得愁雲慘霧。
進公司一年多,連加班費都沒領過一毛錢,卻因為兼個小差,就要被催討薪水。如果這是人與人的關係,這人未免欺人太甚。如今是公司與個人,則公司怎麼做都是對的。
連麻里也狠狠說了我一頓,不是嗎?我一天不還錢,一天就是個「貪婪」的人。
百無聊賴之際,我突然想到:這種糾紛,難道沒有前例?難不成大家都是乖乖還錢?
我決定自己找答案。
和左派打交道
我在網上搜尋,找到了一個「非政府組織」:「勞動者義務支援團體」。
這家位在「青砥」(東京的一個地名)的非營利團體,專門幫弱勢的勞工處理勞資糾紛。我大致瀏覽了這個團體的網頁,找到了聯絡的電子郵件地址。我發了一封信給了這個團體。
「您好:
我來自台灣,自從2011年開始,在東京的○○株式會社任職技術顧問,於前不久離職。
在職期間,我沒領過一分錢加班費,也沒和公司爭取過任何權利。但在離職的這一個月內的『有薪假』期間,只因為我兼了一份差,所以被公司追討一個月的薪水。這對我,一個普通的白領而言,是個很大的負擔。
如您所知:台灣是個對日本友善的地方。儘管有著工作上的不愉快,身為台灣人,仍然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日本依舊是個有效的處世原則。貴團體的存在,更讓我深信這個國家是充滿希望的。
貴團體若能在百忙之中,願意對我、一個外國籍的勞動者伸出援手,提供諮詢服務,我將感激不盡。」
信寄出,我沒多大把握對方會回信。這說不定是個已經沒在運作的團體,甚至只是一個打著「非營利」的幌子,實際卻錙銖必較的歛財集團。我如今只有死馬當活馬醫了。
沒想到,就在信發出後當天下午5點半,回信來了。
「侯桑
您好,我是勞動者義務支援團體的矢部。希望能在本周末務必和您見個面,談談您的問題。恭候您周六下午1:00大駕光臨。
矢部」
收到信,分外高興,起碼自己已經不是在單打獨鬥了。我寫了個信,謝謝對方的回覆,說好周末登門造訪。
不論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,我比起之前的徬徨無助,心裏多了一些對抗的「資本」。4月27日,我單槍匹馬找到青砥這家義工團體的所在。
「您好,我是之前和您們通過信的,姓侯,想找您們的義工,矢部桑」。我對著應門的小姐表明了來意。
「侯桑?歡迎歡迎!矢部桑剛好今天有事,由我來提供您諮詢服務。」小姐一邊說,一邊把我引進了會議室。
「我姓高原,是本會的義務諮詢師。侯桑您目前面臨的問題是…?」高原小姐親切地安排我坐著,主動開口問我要諮詢的內容。
我再把我的問題,口頭向高原說明一遍。
高原聽完,微笑地告訴我:「侯桑,首先,『有給』(有薪假)是員工的福利,不可以用任何名義剝奪,這是有明文規定的。但是你『有給』期間『兼職』的部分…」
「恩?」
「我想,公司是在你提出離職後,給了你『有給』,你的兼職並不會造成公司任何損失。公司沒理由向你討回這筆薪水。」
我聽了,大喜過望。我謝謝她的細心解釋。在這件事情上,我有了一點信心:我那筆錢有希望保住了。
但是,事情是否就這樣結束了?萬一公司不罷休,我該怎麼辦?
公司佔著「資訊不對稱」的有利立場,看準我不知道日本的法令規定,幾乎要把我手中的薪水要了回來。我思索了片刻,做出了一個主動出擊的決定。
「公司在我這一年半的任職期間,沒給過我一分加班費。我還有機會討回來嗎?」
我開口問道。這是一個反守為攻的策略。
其實,在這之前,我仍有兩種台灣人可以做:一、逆來順受,讓人家覺得「聽話好用」的台灣人;二、據理力爭,不和稀泥的台灣人。
前者我做過,但「效果不大」,別人不會因為你的順從而多敬你一分。當我做出「討加班費」的決定後,我走上了後者的不歸路。
高原小姐表情似是一怔,隨即恢復平和的語調:「侯桑,您有證據證明公司積欠你加班費嗎?」
「我不知道要怎樣的證據。公司平日要我們如實報工作時數,但我一旦如實報上去,又被指責,讓我根本無法申請加班費。」
高原小姐聽了,苦笑著說:「這種事常聽說…只是,就算您手邊握有當時加班的紀錄,一旦要爭取加班費,這種加班費的精算,哪怕是日本人也不見得能正確核算得出。」
「那該怎麼辦呢?」我不安地問道。
「恩…我建議您找弁護士(律師)來幫你爭取。連同『有新假』的事情也一併請他幫忙。」
弁護士?那得花多少錢?更何況,哪怕錢都花了,還不確定能爭取得到,那又該怎麼辦?
高原似乎看出我的困窘。她微笑地說:「您放心,有專門為勞工爭取權益的義務弁護士(律師),您可以把您的問題告訴他們,他們會幫您處理。」
高原隨即把她所知道的義務弁護士連絡電話抄給我。那一霎那,我突然覺得:有這群為勞工打拚的日本左派真好!我們來自台灣的人,「右派」幾乎成了我們的基因,誰會在第一時間想到找左派呢?
我不用還錢,甚至可能要回一筆錢。我不僅有了信心,還有了鬥志。
回到家後,我打電話給麻里,把到青砥找勞工團體的事情告訴了她。麻里聽得極為吃驚。我做的事情,完全出乎她想像之外。
「畢竟是日本人呀…」我笑她:「無論什麼事情,你們會第一個想到『對公司不好意思』、『對團體不好意思』,完全站到資本家的立場,忘記自己是個勞工。」
麻里語帶慚愧的說:「確實,從小到大,學到的都是如何爭取團體榮譽,不知道爭取自己的權益。呵呵…。」
我把麻里骨子裡揮之不去的「日本人團體意識」一語道破,麻里上回數落我時的犀利態度,全部煙消雲散。
接下來就是找義務弁護士了。就這樣,我以一個外國人身分,在日本「越玩越大」。(文長未完)
●作者老侯,碩畢,在日本謀生的台灣上班族。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,來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


